“基因编辑婴儿”案,判了!生下的双胞胎女婴该怎么生存?

看到一条新闻,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“基因编辑婴儿”事件,走入司法程序后,今天终于有了审判结果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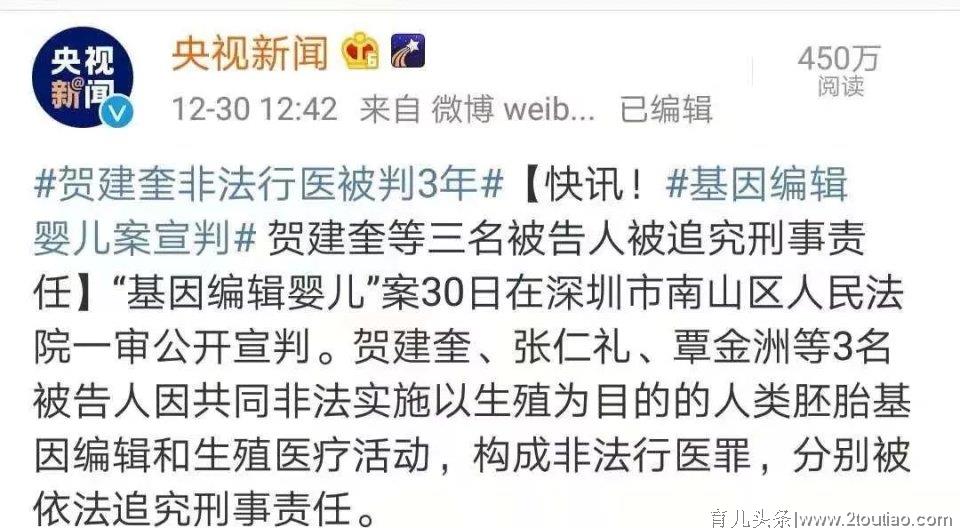
3名被告人构成非法行医罪,判处南方科技大学原副教授贺建奎有期徒刑三年,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;同谋之一张仁礼有期徒刑二年,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;同谋之二覃金洲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,缓刑二年,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。
对于这个结果,广大网友在感到“罪有应得”的同时,也纷纷为成为“试验品”而诞生的无辜婴儿感到担忧:

这件事虽然过去一年了,但作为一个妈妈,我今天看到“基因编辑婴儿”这几个字还气愤不已。我们来回忆一下整个事件:
2018年11月26日,微博头条新闻发布了【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】的消息:
由科学家贺建奎主导的“基因编辑婴儿项目”,在至少7对夫妇的受精卵上修改了一个名叫CCR5的基因,使其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。
并且其中一对夫妇的双胞胎婴儿已在中国诞生,取名露露和娜娜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,在网民们还在试图理解什么叫“基因编辑”时,事情反转,一众科学家开启了联名谴责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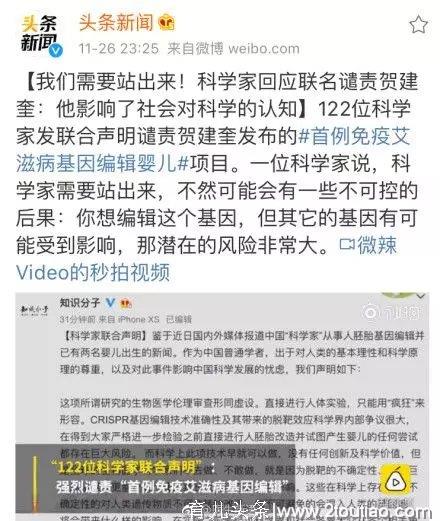
在这份联名谴责书里,科学家们主要提到了5点:
1. 贺建奎这项“基因编辑”项目所谓的伦理审查申请书来自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,一家“莆田系二代”医院,其伦理审查程序如同虚设;
2.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尚有脱靶问题未解决,风险很高;
3.编辑基因带来的不确定性太多,对人类群体的潜在风险和危害不可估量;
4.对中国其他遵守道德底线的科学家不公平;
5.让中国科学家的声誉在国际受损。
“修改基因”、“人体试验”、“艾滋父亲”、“编辑婴儿”这样的字眼,每一个都让我觉得窒息。
当科学可以超越伦常、当基因可以随意编辑、当孩子可以独家定制,这样“进步”的未来世界,人的存在究竟还重不重要?

孩子不是产品,可以随意改造
为什么这个实验必须受到谴责?
第一,双胞胎父母中只有父亲是艾滋病人,母亲并未被感染;
第二,艾滋病是性病、传染病,但并不是遗传病,现在可以通过母婴阻断技术生下健康孩子。

贺建奎的“基因编辑婴儿”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非法人体实验。
所谓的“基因编辑”,现在是从预防的角度去改善基因,但后期难保不会演变成人体基因的完善。
我想要个大眼睛的,你想要个高鼻梁的,我想要个性格乐观的,你想要个皮肤白的......
当基因可编辑,“孩子”就像流水线的产品,人性和文明早已被摒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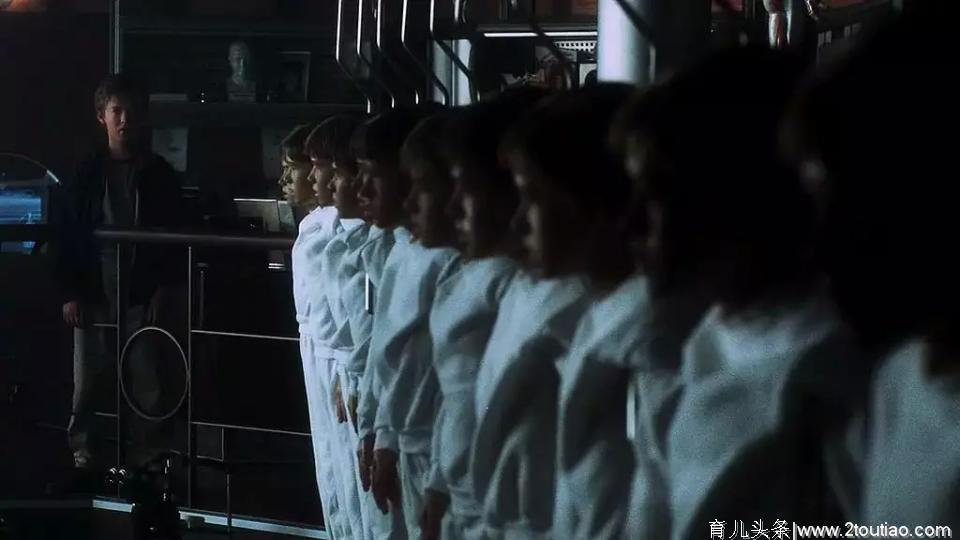 来源:电影《人工智能》
来源:电影《人工智能》而隐藏在这背后的,是仍然把孩子当做传宗接代的产物、当做自己私有物品的落后观点。
所以这项所谓的“基因编辑”技术究竟是科技的进步还是观念的后退?不证自明。
上周跟同事做绘本故事分享时,在讲到《猜猜我有多爱你》时,我说了一段话:
“孩子,不要让我猜有多爱你,我对你的爱,超出你猜测的很远、很远......”
有同事打趣说:“等你孩子上了小学,需要辅导作业的时候,你可能就爱不起来了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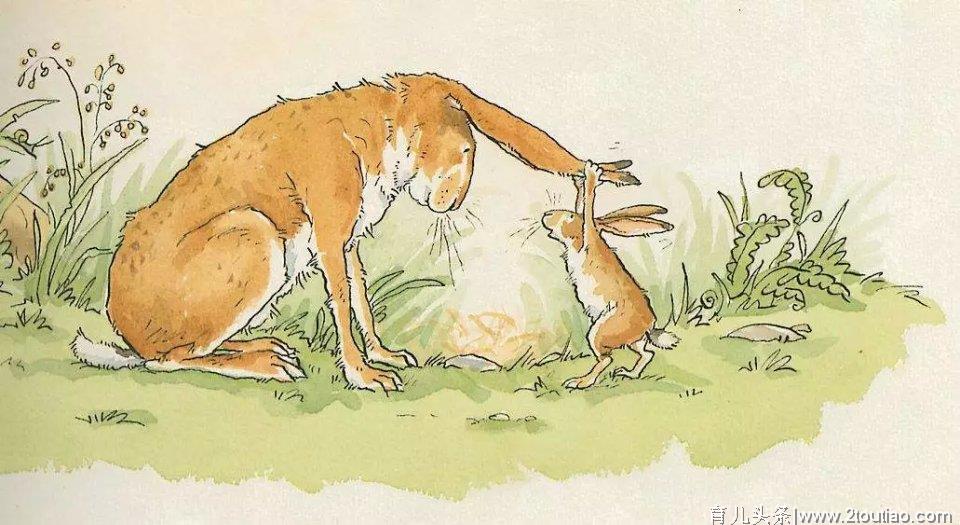 来源:《猜猜我有多爱你》
来源:《猜猜我有多爱你》然而事实是,我们会因为孩子的某些行为生气,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但不论何时,我们对孩子的爱都不会改变。
记得几年前刚怀孕的时候,一开始也担心过:
“万一我的孩子长得不好看,万一我的孩子很笨,万一我的孩子性格不好,我会不会没那么爱他啊?”
可随着怀孕时间的推移,到孕晚期,这种匪夷所思的念头再也没有过。

怀孕25周做大排畸时,突然被告知羊水异常,可能引发胎儿畸形,须转诊到上级医院做进一步确认,时间约在了一周后。
在这之前,说实话,我除了生理上的变化,心理上对肚子里的孩子没有具体的概念。
但现在,我能想象出他有圆圆的脸,胖胖的手臂,咧着嘴,笑着叫我妈妈,他会长大,会上学,会有叛逆期,会嫌我唠叨,会跟我拌嘴吵架.....
一切都变得真实起来,我突然发现非他不可,我只想要这个孩子,只想要他。
等确诊的这一周里,我备受煎熬,度日如年。
也让我意识到:妈妈的爱只有一个条件,那就是——你是我的孩子。

不论你什么长相,不论你什么智商,也不论你什么性格志向,只要是你,便好!
我们爱孩子,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可编辑。
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去设定别人的生命和人生。

编辑基因,只会让孩子的未来更不公平!
关于编辑基因对未来孩子带来的影响,王立铭老师这段话已经论述得很清楚了:
“如今,尽管存在一系列各种资源和能力的不平等,但一切至少是有可塑性的。
家境贫寒的孩子努力读书工作仍然可以出人头地,优越的家庭条件也有‘富不过三代’的永恒困扰。
但是如果有了基因编辑技术的介入,一切就有可能不一样了。如果一部分人的孩子早早接受了基因编辑技术的‘改善’他们就可能从外貌到智力各方面都占据竞争优势。更要命的是,这些优势还是写进基因组里、可以遗传的,那么其他的孩子可能就永无翻身之日了!”
人类基因的出厂设置已经让我们从起点上有了小概率的不公平;
人类社会财富地位、教育资源的不同,也让我们未必在同一起跑线。
但至少我们还有改变的机会,还有既定的秩序去保证相对的公正。

举个不恰当的例子,“基因编辑”就像是人体硬实力的整容。
同样是为了变美,健身跑步,受到肯定,而整容却往往遮遮掩掩,甚至被嘲被指指点点。
原因不过是——整容是变美的捷径,是不公平竞争:
“我苦兮兮地顿顿吃草节食、天天健身撸铁,
终于在半年后减重20斤,化上淡妆也能被夸“可爱”;
而你,比我颜值低、体重高,只去了趟医院,不到一月,脱胎换骨,化身女神,拿到我想要的offer,牵手我努力想与之匹配的男人。”

同样的,接受基因编辑的孩子,对其他孩子来说极其不公平。
未来,他们将在基因的金字塔尖享受各项权利,甚至控制奴役未接受基因优化的孩子,并开启世袭制。

“定制婴儿”,违反人理伦常
作为一个妈妈,我反对“基因编辑”,还有伦理道德上的担心。
当基因技术已经可以改造或制造新的人类,那么这些“被编辑过”的人类,到底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“人”?而我们的孩子未来要怎样与他们相处?
这样的场景在很多科幻电影里有过:
电影《银翼杀手2049》里瑞恩.高斯林主演的K,从一开始就告诉观众他是复制人,而且K也清楚自己是复制人。他的工作是猎杀旧型号的复制人,可那些复制人也有自己的情感,也都爱与被爱,试问,又有谁能扮演上帝,去决定这些生命的生死。
在影片发展过程中,K从自己是复制人,到认为自己不是复制人,又回到自己是复制人,一波三折,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中受尽折磨。
 来源:电影《银翼杀手》
来源:电影《银翼杀手》这对“基因编辑婴儿”露露和娜娜以后将面临什么?
作为人体试验的“小白鼠”,会不会像《楚门的世界》一样活着?
上海大学社科学部哲学系教授周丽昀曾说过:科学研究可能无禁区,但是科学的应用一定是有限度的。科技与伦理之间是存在博弈的。如果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匹奔驰的骏马,那么伦理就是制约它的缰绳。
“定制婴儿”和“完美宝宝”的出生违背生命本身的伦理规律,也损害“基因编辑”的生命体的人格尊严,违反宪法、民法中关于人格尊严保护、胎儿利益保护的相关实体规定。
科学最后的底线,就在于不该挑战“人性”。
而孩子,从来不是被制造出来的物品,自由和爱才是我们应该给予的东西。
真正的爱,是如他所是,而非如你所愿。